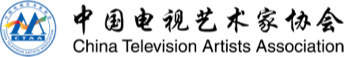
欢迎访问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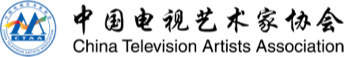
 文化观察
文化观察
叶少兰:我们要继承什么
◎京剧表演不是说出,必须通过真功夫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只学会了不行,要学对了才行,就连最简单的一踔一站,一个弓箭步,一个蹲裆式,一个山膀、云手,也必须是京剧的、本行当的、规范的,而后才能说其他。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1949年从艺至今已60余年。上世纪50年代,我有幸目睹并经历了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成各个流派的艺术家们的创造过程及他们创造出的辉煌艺术。改革开放后,戏曲事业又出现了创新的发展高潮,涌现出一批新的领军人才,可喜可贺。在把戏曲继承发展工作做好的同时,一些现存问题还需要认真解决,更重要的是要取得共识。
首先,这体现在对京剧特性的认知上。有些条件好也努力用功的演员未能得到很好的发挥,问题出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作为京剧专业的演职员,首先要认清继承什么,然后是如何发展,做到有的放矢。
我在哈佛大学、香港大学以及纽约联合国总部教科文组织的学术活动中,都做过关于中国京剧的综合艺术特性的专题讲座。京剧不是单纯的武术、功夫和单一的歌唱。京剧有文学剧本、故事情节,有人物性格、矛盾冲突,是用歌唱、舞蹈、朗诵、表演、武术、杂技、音乐、美术、服装、头饰的综合艺术形式来表现人物故事情节的。京剧最大的艺术特征和表现手法是不受时空限制,表演上是虚拟、夸张、写意、程式化而又有生活依据的,是载歌载舞地在舞台上讲故事。“凡声必有歌,凡动必有舞,处处有音乐,风景随人行”(盖老的一句话:这就是京剧),风雨雷电,马嘶人啼,音乐一概可以包办。一份戏箱(服装道具)可以表现上下五千年。因此说它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艺术综合性最强的表现手法,是被誉为国粹的伟大艺术。
京剧行当分工之细,脚步分辨之严、之讲究,跟斗、把子的艺术化,锣鼓、音乐的程式化,服装的划分与讲究,脸谱并非任意勾画和它的故事性、生活性……都有非常独到的地方。我们专业工作者必须认识它、掌握它,才能运用它;必须原原本本地继承它,才能宣扬它、发展它、建设它、爱护它,对事业没有感情就不存在敬业和创业。
这样看来,老师就要使专业演职员学会选择用不同的技术手段为不同剧目服务的本领,明白表演技术的依据,从而提高艺术修养,避免出现“我也不知为什么这么演、这么做、这么唱、这么舞,我就这么学的,录像就是这样”之类的话。因此,跟随录像学戏应该只是个形式化的学戏方法。如果不学会、不理解表演的缘由和设计的根据,表演一定是貌合神离、动作漂浮、莫名其妙的。这种情况时有出现,核心在于学得不深,基本功不扎实,或继承不够,不到家。
我以为,一个戏,你理解越深,表演才越活,自己要求也会越严格,心里有谱就充实了,有了底就会找到最好的感觉和信心。有过教学和舞台实践的人都会有这种体会。我们说音乐、唱腔有谱子,身段、表演、服装、道具同样要有谱子,这就叫规范。所有单谱在一个剧目中都要综合成一个总谱,只是这个谱不再铺在架子上,而是在你的心里和身上。凡是一个优秀的剧目必有一套优秀的总谱,只是我们没有整理出来,只在口传心授之中。老师经常向学生发问“你有谱没谱”或说“你这没谱呀”,就是这个道理。
当一名戏曲演员提高的时候,一定是他明白的时候。好多小地方的表演,我们把它漏掉了,或认为没什么必要了,或走个路子淡化了,但这常常是精华所在,正是表现人物特性的重要地方。比如“群英会”中周瑜的几个小地方:盗书时的“看书”、“摸黑”等,翎子的来源与用法,各种胡子的用料和运用,甩发的长短,都需要了解、继承。
对待京剧唱念特征的认知更是如此。在打基础的时候不能只注重嗓子和流派,还要加强音韵和诗词的学习。京剧讲四声、音韵、十三辙、湖广韵、尖团字,既有方言特征,又有诗词规律。诗词、二簧要熟知,昆曲、吹腔也要知道。
四大徽班以“四喜班”的曲子最有实力,当时被称为“四喜班的曲子,三庆班的轴子”。三庆班善演整本大套的长卷戏,轴子是指一边看一边卷的长卷画轴,那时候开场叫早轴子戏,中场叫中轴子戏,最后的叫大轴子戏。三庆班阵容最强,常演三国、列国、水浒一类的故事。生、净抬头,唱大轴就是从三庆班开始。当时还有“和春班”的把子,即以武戏见长,清代把刀枪剑戟等兵器叫做把子。军旗、把子放在一起叫旗把箱。戏班中加之道具叫做奇宝箱。舞台的武打套子、武打教学场称为把子功、把子课。徽班的另一个戏班子被颂称为“春台班”。此班学员甚多,小孩天真无邪不知取巧,台上人多热闹。后来由于演出多、学得少,很多人才未遇良师而夭折。在嘉庆二十五年和道光十三年,以孩子著称的春台班和以把子著称的和春班先后解散,这是个经验教训。由此可见戏曲表演的综合实力和人才的实力培养有多么重要。
再谈唱念特征的认识问题。“群英会”中周瑜点绛唇,手握兵符,我们把“握”唱成“要”字音,有人在字面上改为“要”和“摇”,这是错误的。在《五方元音》《韵学骊珠》的资料中均可以查出,当时的曲律中“握”就唱“要”音。在元曲、昆曲中,变韵脚是有的,我们舞台上至今也在应用。“说客”念“shui客”,至今我们社会生活中、媒体中仍然应用,“行”字也如此。许多民族历史文化特征还在京剧昆曲里保留着,这也是我们继承发展创新工作中的一大课题,更是国粹的价值所在。
京剧舞台上曾经有很多优秀的京剧曲牌,都是又有气氛又极有历史感的曲子,现在已经听不到了。我想主要还是因为没有传授和要求,或者不了解而流失于舞台。上世纪50年代在巴黎观看“雁荡山”的观众会激动地站起来,现在不那么疯狂了。我并不主张跟他们比,京剧就是京剧,但我主张出新和提高。我们必须看到时代的需要,两百年来,京剧从来未离开过时代。
一个合格的表演人才不仅要会多少,而且要对多少,会和对要一致、统一才行。会是知道,对是实践,把会的通过实践准确表现出来,才是一个合格的演员。京剧表演不是说出来,必须通过真功夫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只学会了不行,要学对了才行,就连最简单的一踔一站,一个弓箭步,一个蹲裆式,一个山膀、云手,也必须是京剧的、本行当的、规范的,而后才能说其他。京剧讲究站如松,走如风,坐如钟,躺如弓,这在生活中就应养成习惯,何况我们的职责是表现高于生活的舞台历史的基本形象。
我想,国家对戏曲如此重视,一批专业人士尚在埋头苦干,继承延续,呈显希望,中国的戏曲艺术一定会再现辉煌!
(叶少兰 第九次全国文代会代表)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叶少兰
责编:视协网